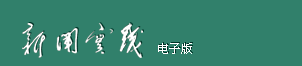| 祝云光2003-6-1 在抗击非典的战斗中,百姓最关心最牵挂的,是医院隔离病区内非典病人的病情和和医护人员的健康,以及数百个隔离点内的居民。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他们是如何度过这段非常生活的?这些信息,由于被采访对像处于严格的隔离之中,记者的直接采访异常困难。
4月28日杭州一张早报头版上的一条消息,吸引了电视人的眼球。这篇配有照片的《真想告诉你,这里有多少感人故事》的文章,报道了在水一方隔离区内一位姓张的大姐,用DV记录了楼内居民的隔离生活及他们的真情实感。照片上,铁门后戴着口罩的张大姐,隔着单元门的铁栅栏将一张白纸伸出门外,上面写着“是否需要隔离区居民点的生活工作录像?”,并清楚地留下了联系电话。这不正是电视人苦苦追寻的东西吗?报纸刊登当天,张大姐家里的电话被打爆了,其中大部分是杭州的一些电视台打的。下午,电视台把一根电缆线接到张大姐家里,通过这根电缆线张大姐把自己拍摄的内容传了出来。很快,张大姐拍的新闻《在水一方:我们是个互帮互助的集体》在浙江卫视最重要的新闻栏目《浙江卫视新闻》中播出了,片中的旁白还是张大姐自己的声音:“今天我们又要发比萨饼,发净菜,我们要把每家每户的净菜都安放好,等待每个业主来领……”张大姐现场拍摄现场描述,还“采访”了一位精神很好的老伯,朴素真实地展现了隔离区内的百姓生活和非常时期的邻里情。
受此启发,浙江卫视另一强档新闻《新闻观察》索性给在水一方的每个家庭发了一份征稿启事,希望有摄像机的家庭能拿起机器,用镜头记录自己的生活,记录这段非常的历史。在杭州某中学电教室工作的祝女士欣然报名。从4月29日到5月2日解除隔离的三四天时间里,她用手中的DV,拍了总共180分钟的素材画面。5月3日,13分钟的新闻专题《被隔离的日子》在《新闻观察》栏目播出。
新闻自己拍,在一些城市台早已不新鲜。这里,笔者从传播学的角度,从传播者—媒介—受众这三个方面,探讨DV进入电视传播的理由以及对传统传播理念带来的变化。
一、DV:寻找与电视媒介的接点
1、家用属性。
曾经有专门研究收视行为的学者对一定范围内的城市居民做过一个调查:你回到家中第一件事情干什么?其中40%以上的人在第一个答案中选择了“打开电视”,75%以上的人在前三个答案中选择了“打开电视”。由此可见,“看电视”已经成为人们、尤其是城市里的人们的一种生活习惯,是人们在家中的一个“标志性”行为。所以,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孙玉胜在他《我看电视》一文中就提出,电视是一个“家用媒体”,或者说,电视具有“家用属性”。
那么,什么是DV?DV就是DigitalVideo,数码视频摄像机的缩写。它采用了数码信号的方式,能够达到500线以上的影像扫描,其播放质量达到了专业摄像机的图像质量,音质达到了CD级质量。现在普通DV机的价格一般在5000元—14000元左右,而且这个价格还在往下降。较高的性价比和轻巧的机身,是DV正以加速度进入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
2、娱乐“壳”、信息“核”。
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是这样看待电视的:大多数人打开电视,是为了看电视剧,看娱乐性节目。而大多数人打开报纸却是为了读新闻,了解本地和世界上发生了什么重大新闻。因此,电视强调的是娱乐色彩,而报纸强调的是真实的新闻报道。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通常把电视归类于娱乐界,而把报纸归类于新闻界的原因。但另一方面,许多人又是从电视上获得新闻的。如果问一个普通百姓:新闻媒体是什么?他往往会回答:“电视”。
为了娱乐而打开电视,却得到了信息。这个有趣的现像也同样发生在DV使用者身上。有人把DV比作卡拉OK,说它纯粹是自娱自乐。他们可以拿着DV去拍电影,拍短剧,但更多的人是在记录着生活的一点一滴,就像拿着相机一样,只不过拍的是动态的影像。南方周末的一项调查显示,拿到DV,人们最想拍的就是记录片,占43%。
看来,DV与电视之间的确存在许多的相似之处,而正是这种相似性,注定了两者从开始约会到最后结合,轻松自然水到渠成。当那天浙医二院ICU主任崔巍,将一盘经过消毒的记录有非典病人抢救情况的DV带从隔离病区内传递出来时,更加坚定了笔者的判断:一个不可阻挡的个人影像时代已经大大方方地到来了。
二、DV:打破专业人员影像话语权
1、尊重受众的参与权。
受众不仅有知晓权,还应有参与传播的权利。但是由于不同的传播媒介具有不同的特性和功能,其被允许的参与程度也是各不相同的。
以冷热的性能作比,麦克卢汉将媒介一分为二,电视被列入冷媒介。在麦氏看来,冷媒介作为低清晰度的媒介,提供的信息较少,明确度和完备度较低,因而需要接受者积极参与、发挥想像力,努力填补媒介在传播中留下的许多空白和“回旋余地”。麦氏的理论艰涩难懂,但电视需要受众参与却是谁都能听懂的。而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参与正变得越来越现实和直接,因为有了DV。
2、打破少数人对影像话语权的垄断。
人人都有表达的权利,也叫“告诉的权利”。而DV就给了大众这个权利,一个影像表达的权利。如今很多电视台已经接受DV爱好者拍的影像作为节目内容,中央电视台《金土地》栏目播出的《开拍啦》,全部节目都是农民用DV拍摄的。在一些城市电视台,这一形式被运用得更为普遍。众多的“编外记者”,较之职业记者情感更纯朴直观,其非专业的眼光,有时恰会给人带来一些格外的惊喜。
3、影像话语权不再是男性的专利。
多少年来,对摄像机的掌控,一直是男性的“专利”。几十斤重的专业摄录器材,硬生生地把女性拒之门外,那可是个体力活。女记者无论去哪都缺不了摄像跟着,否则就干不了活。
但DV却让这一切慢慢改变。独立电影《盒子》导演英未未认为“DV是对女性的解放”。在她未接触到DV之前,常常感到电视台里那种笨重的家伙无力掌控。但是DV的轻盈和易操作使她“拿起机器去创造影像成为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女性摄像者的出现,将使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更加完整。因为先前我们一直是通过男性所拍摄的影像,来认识这个世界的,别无选择。而现在通过女性影像,我们会发现世界可以这样的,还可以是那样的。”本文前面曾提到,《浙江卫视新闻》和《新闻观察》栏目都播出了居民自己用DV拍的隔离区内的报道,而两位拍摄者都是女性——张大姐和祝女士。在祝女士的镜头中,有喜欢讨论天气的老人,有一起玩呼啦圈瘦身的母女,有一边做作业一边又等着同学电话响的小学生,还有不同家庭订的不同伙食……亲切自然美好,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如果感觉敏锐是诗人的一个基本要素的话,那女性就先天有这种诗人性,女性影像即便对准的是困境中的人们,也会让观众感觉诗意。可以预见,未来会有更多的女性加入到影像采制的队伍中来,正如大街上开汽车的女性越来越多一样。
三、DV:放大“自己人”效应
自己人效应是指受传者在信息接受活动中感到传播者在许多方面与自己有相似或相同之处,并在心理上将其定位为“自己人”,因而提高了传播者的影响力。那么DV传播者是否是受众的“自己人”呢?从所持的立场分析,DV拍摄者不是电视台的专业记者,而是百姓中的影像爱好者,它是一种私人的创作,摄制者与被摄者之间能够产生真正的平等。在DV面前,被摄者以往在电视台记者的大机器面前的拘束和恐惧没有了,记录者可以记录下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以往困扰电视人难免干涉生活的“镜头暴力”被可能还在变小的DV化解了。当然,机器大小本身并不会对被摄像者有多大影响,大机器背后所代表的组织才是被摄者感到不平等的真正原因,而DV后面的只是个人,而不是一个组织一个集体。
从身份背景来看,DV爱好者来自各行各业,更具有大众的代表性。在杭州电视台“新闻自己拍”俱乐部30多名成员中,有大学教师、律师、工人、自由职业者、婚庆摄像师,年龄最大的76岁,最小的才十几岁。他们在工作生活之余,用手中的DV捕捉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新闻,成为电视台“零距离贴近”理念的一种崭新实践。
科技的一日千里把DV带到人们面前,也带到了电视媒体面前。习惯了沉重的电视实在没有理由拒绝轻盈的DV。DV是数字格式的,可以在个人计算机上编辑,也可以在互联网上传播,双向互动交流极易实现。如果今天的电视不能承受DV之轻,不能学会平等地对待它真诚地接纳它,那若干年后的某一天,电视或许就要不堪承受其重了。
|